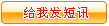 |
 |
风云  |
 | | 等级:三副 |
| 经验:2904 |
| 积分:1338 |
| 博客:到我博客逛逛 |
 本帖荣获 本帖荣获 |
鲜花: (0支) (0支) |
鸡蛋: (0枚) (0枚) |
  |
|
性的经济学分析
(一)
对我来说,性是一种珍贵的稀缺资源,当然,我指的是性生活,而不是性别,性别我自己也有一个,这是我快乐和烦恼的根源,用经济学的术语说,就是成本,这成本在有生之年能给我创造多大的价值和效益,或者赔个一毛不剩,变成呆坏帐和闲置资产,我心中还十分没底。
波茨纳说,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。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:如果我知道茱迪.福斯特染上了艾滋病,那么不管我多么仰慕她,也不会跟她上床,这事风险太大。这说明作爱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,有需求,有供应,有风险,有收益,还要计算投入产出比,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贝克尔断定:上帝目光所及,皆可交易,那么毫无疑问,深藏床帷之后的性爱和农贸市场上的萝卜具有某种共性,这也符合波普艺术家们的价值观,1954年艾伦.金斯伯格接受记者采访,说世上并无尊卑,如果有不平等,那也只是价格上的不平等。我觉得既然谈到价格,那其实还是一种平等--钞票面前人人平等,比如香港的淫媒组织就曾经列过一张菜单,把演艺界的女明星一网打尽,我心中的那些偶像,从清纯玉女到三级肉弹,谁值多少钱标得清清楚楚,如果我手上有一亿美元,那感觉就象走进了超市。
不考虑宗教信仰和道德的负面影响,那么一次单纯的、形而上的性爱就是一个契约,酒店里的桑拿小姐问先生要不要服务,可以视为一个要约邀请,至于老婆掐着老公的脖子发令:官人,我要!就明显是一个标准合同,不明白标准合同的朋友们可以这么理解:虽然你反对手机双向收费,也不满意中国电信的服务,但你还是要入他们的网。
合同订立后的性爱象一单混合了FOB和CIF特征的国际贸易,FOB的意思是船上交货,货物在越过船舷之前,发生任何毁损灭失、遗弃泄露都不能算是交易成功,失败后的男人们一个个垂头丧气、额头冒汗,这充分说明作爱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,而“哪里有风险,哪里就有保险”,于是就有了杜蕾丝、拉士丁和杰士邦这些品牌,根据弗里德曼的“假设不相关论题”,我们可以断定杜蕾丝和中国人寿作的是同样的生意,而第一个把避孕套叫作“保险套”的人堪称伟大,他要不是天才,就一定是个经济学家。CIF术语指的是货主承担成本、保险费和运费,所以到药店里买避孕套的大多都是男性,交易过程中,出力最多、忙前忙后的大多也是男性,货主嘛,规定要承担运费的。
如果探究到细节,性爱合同比其它合同更加完备:除了交货、验收,它还有交易后的信息反馈机制,电影《一声叹息》里,张国立问刘蓓:好不好?刘蓓娇喘一声:好死了。看得人心潮激荡。当然,这种反馈机制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完全对称,上海有个美女写了一篇文章,大标题就是:《伪装高潮也快乐》,这明显是在号召提供虚假信息,如果这种作法如果被会计师事务所学了去,必然会引发信用危机,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。我在此要引用的第二个案例是美林证券,这家世界闻名的证券公司因为提供虚假投资评估,2002年被罚了一亿美元,那笔钱如果给我,我就有能力去逛逛超市了。
(二)
对体制内的交易双方来说,性象一块永远嚼在口里的口香糖,它的好处是随时都有东西让你咬,不至于空虚,不至于闲得牙疼;缺点是越嚼越无味,到最后就成了一种纯粹的习惯。“七年之庠”的说法,不仅说明消费者对单一产品、无差别服务的厌倦,也证明了性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效用递减:最开始拉拉手精神抖擞,亲一下浑身颤抖,但后来拉得越多、亲得越多,这事就越没有吸引力,美国一个无聊的民间调查机构统计了三百多对夫妻的睡姿,最后得出结论:婚龄半年以内的夫妻,大多是面对面搂抱着睡,婚龄超过2年的,几乎百分百是背对背睡。这些姿势和体位,我们可以看作是人性化的市场需求信息。还有一位专攻下三路的诗人说,他在婚姻中唯一获得的“体制性的阳痿”,看来他需要到消费者协会去投诉。
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就在于“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”,薛兆丰说婚姻是“终生批发的期货合同”,这些都说明婚姻是一个规模经济,规模经济与单干户相比,优势主要在于两点:一是成本小,没结婚的两个人需要两张床,结了婚就只需要一张;二是可比价格低,香港报纸上有很多色情广告,广告卖点多是皮肤、身材,或者武功,从来没见过有小姐宣称自己价格低,“跳楼价、大出血、拆迁甩卖”什么的,因为她们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优势--老婆是不用花钱的,所以只好在差别化服务上作文章。
性市场大概是唯一一个供应不足的买方市场,一方面,小姐们纷纷抱怨“生意越来越难做”,另一方面,体制内外的男人们都在进行着DIY,这情形有点象我们经历过的“以计划经济为主,市场经济为辅”。我表哥那时候曾因为“投机倒把”坐了几年牢,出来后赚了一点钱,据说养了好几个二奶,然后我表嫂就开始留指甲,时常偷袭他。这两种审判说明投机倒把始终是一种背德恶行,而走私更加不可饶恕。但根据我表哥的供述,他也确实值得原谅,我表嫂出身名门,教养过人,对作爱有近乎苛刻的要求:要洗澡,要关灯,要遵循法定程序,要正面交流,决不可暗度陈仓,等等。这大大提高了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,用经济学的术语讲,就是高关税壁垒,我表哥不懂经济学,他用最朴素的话表达他的意见:真他妈没意思。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利润问题。
张五常在中山大学演讲时,说交易成本越高,人就越穷,交易成本降低一点点,人民生活就会快乐很多。这话简直就是我说的。法国人心中的完美妻子是“客厅里的贵妇、卧室里的荡妇、起居室里的仆妇”,这其实也是在响应张先生的理论:降低交易成本。我表嫂因为她长期供应的质次价高的性产品,终于在1999年被我表哥取消了交易资格,他们离婚了。这对一直持币待购的投资者,我,是一个沉重打击,从那以后我见人就说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。
(三)
前些日子各地都有“换妻俱乐部”的报道,我这个人有点趣味低下,遇到这样的新闻,总要反来复去地看。《圣经》上说“亲近邻舍之妻的,不免受罚”,所以搞换妻俱乐部的这些家伙,最后全都被捉将官里去,打板子,捱班房,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,没资格参与这种非法活动,见了总不免有点幸灾乐祸。
换妻这事可以算是一种等价交换,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,交换是一种增值行为,农民拿粮换布,是因为他织布要比种粮食花更多的时间,这种交易让他节约了时间。由于没有人想作亏本买卖,所以换妻肯定也是一种增值行为,前面说过了,夫妻之间有个“性的边际效用递减”问题,“李杜诗篇万口传,至今已觉不新鲜,”而换妻则可以解决生产中的设备老化问题,以自己的不新鲜换别人的新鲜,使效用大大提高。萨缪尔森有个幸福公式:幸福=效用/欲望,在欲望不变的情况下,效用越高,就越幸福。所以换妻事实上是一件幸福的事,但这结论显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。
经济学中有个名词叫“帕累托优化”,是指在资源分配中,不损害他人福利而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福利,1980年华罗庚数学竞赛有这样一道题目:大家排队取水,桶各有大小,怎样排列才能保证总体效率最高?答案很明显:小桶在前,大桶在后。但这损害了大桶者的利益,所以它是一个伪帕累托。阿瑟.奥肯1975年的“漏桶试验”,损害富人的利益来帮助穷人,是另一个著名的伪帕累托。照我看世间真正的帕累托优化不多,而换妻就是一个。它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--大家自愿,换过后也不影响使用,但每个人得到的效用都大大提高,当然这里必须排除性病传染的因素。
几单位的性资源换一辆保时捷,可能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值,也付不起,香港某位著名女星还换了一套几千万的豪宅呢,你怎么说。不过这也正常,交换总会有价格问题,电影 《不道德的交易中》,黛咪.摩尔的老公拿她换了一百万美元,事后十分痛苦,觉得这生意不划算,如果他换来的不是一堆钱,而是别人的老婆,想来就会好过一些。
换妻应该算是男人的恶行,网上有些女网友评论,说这样的男人真恶心,拿老婆当玩物。这话看似偏激,实则非常接近真理--性其实就是种物权。物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排他性,你买了一只锅,这只锅就只属于你自己,别人不能轻易碰。性也是这样,尽管老婆大多时候都闲着,但谁也不会让别人轻易使用,也许变态会这么干,但我从没见过。再说说网上评论的事,女网友评论完了,有个男网友在后面骂,骂得十分提神:三八,你们怎么不说那些当老婆的,她们不也在换夫吗?
当然,换妻这事最终是个道德问题。经济学要不要兼顾道德,这事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吵个不停。但道德这东西谁能说得清呢,除了上帝。宗教主义者认为上帝是人类最终的理性,这话可以跟波茨纳那句“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”联系起来理解。《圣经》里是这么说的:“艳丽是虚假的,美容是虚浮的,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值得称赞。”这话有点费解,如果我有个老婆,让她怕耶和华我没意见,但非要她敬他爱他,我就觉得他是在占我便宜,单方面的我不干,要就换妻。
(四)
按古龙的说法,性产业是最古老的职业,“堪为百代祖师”,那时候没有钞票,人们拿贝壳换粮换米,我怀疑有些人收藏贝壳就是想回到原始社会。根据伪学者慕容雪村的考证,“性”这东西可以算是另一种贝壳,每一单位的性资源换多少张狍子皮,换几捧高梁米,大概早有定数。即使到了现代社会,性依然是万能结算工具,可以换彩电,换房子,换工作,换城镇户口,有个美女还拿它换了一个法官当。所以英国前首相狄斯.赖利说“货币是唯一比爱情更让人发狂的东西”,这里的“货币”如果不是指性资源,我就觉得不大好理解。
站在动物的立场,人类的性压抑、性苦闷实在是不可理解,93年春天我去北京动物园玩,看见一只老虎四脚乱跳,咆哮不止,据说是发情使然。想想这些动物们也真可怜,一年只有那么一季,还不容易遇见合适的对象,茫茫林海,真爱何求啊。人类就不一样,一年到头都不闲着,自带设备搞生产,方便又轻松,资源又丰富,没有稀缺性。经济学中的“稀缺性”指的是对需求而言,资源总是有限的、不足的。这种理论应该不适用于性资源,人类的性需求十分有限,“百年三万日”,这数字大概可以算是人类的极限,即使威猛强悍如张伯伦,也有支撑不住的时候。与这有限的需求相比,人类拥有的性资源可以算是无穷无尽的,50亿人口中有一半都是异性,如果我们也是老虎,肯定用不着四脚乱跳,咆哮不止。
一个开放的性市场需要制定交易规则,这是套用康芒斯的话。为了避免性市场陷入萧条,政府应当以行政干预拉动需求,比如对性产业免税等等,这大概可以算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。不过在现阶段的中国,康芒斯和凯恩斯们都无用武之地,性产业不合法,从业者只好在地下状态左躲右闪,偶尔生产,这显然不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。就象爱伦.坡的诗:被光明弃绝/向幽暗中寻找自我。这诗是我查字典翻译的,不知道译得对不对,但2000年我曾见过一个被收容的姑娘,她这样对警察说:找不到工作,摆个摊你们又要没收,不干这个干什么?那姑娘如果会用英文写诗,中国可能要多一位女文豪。
红灯区合法化的问题,在全世界都有争论,反对者认为性产业合法化会导致伦理危机,上帝是这么说的,“妓女如深坑…她埋伏好象强盗,她使人多有奸诈。”上帝的比喻总是很形象。除此之外上帝还说了一句:“与妓女结交的,浪费钱财,”事实上有钱不用才是恶行,因为那将导致经济危机,否则政府拼命拉动内需干什么。18世纪初,英国医生伯纳德.曼德维尔写过一首诗叫《蜜蜂的寓言》,说节约并非美德,奢侈浪费才是致富之道,这诗对凯恩斯有莫大影响,但明显跟上帝过不去,所以被禁了好几百年。反对者的第二个理由是性病,认为红灯区合法化就是性病泛滥的前兆,这话也有事实依据,比如泰国就有爱滋病泛滥的问题。
我个人倒是赞成合法化,但谁如果认为我这是为了自己嫖娼方便,我也无话可说。我的观点是这样的:既然不可能禁绝,不如拿它来赚钱。一个阵地,政府不去占领,黑社会就必然去占领。钱在政府手里和在黑社会手里哪个更能为广大人民造福,这事不好说,但逃税总不是美德。至于“伦理危机”,我看就是个幌子,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,米蒂亚这样告诉阿辽沙:关于伦理学,我没法对你解释清楚。根据我的个人经验,所有解释不清楚的东西都会成为幌子,比如雷公电母、狐仙和柳树精,乡村巫医们靠着这些发了老鼻子财了,但最大的一个幌子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。再说说泰国的爱滋病,据我分析它不是红灯区合法化的问题,只是政府管理不当,如果不合法,可能传染得更厉害。众所周知,地下状态什么东西都传播得快,比如小道消息、黄段子,还有SARS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,荷兰鹿特丹曾打击过色情行业,结果政府税收锐减了几亿盾。据说太原也有这种情况,但身边的事不好说,我们还是说别人吧。
(五)
作为一名独身主义者,我坚决认为婚姻是个赔本买卖。首先它的机会成本太高,我们形容某人得不偿失,常说他“捡了芝麻,丢了西瓜”,那么结婚就是捡了一粒芝麻,却丢了一个谷仓。投资理论讲“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”,而结婚显然是违背了投资理论,你把所有的蛋都放了进去,最后却未必就能孵出小鸡鸡来,弄不好连蛋都要打破。
前些日子广东有个案例:有个人在外面包了个二奶,老婆发现后怒不可遏,一刀将他的作案工具割下来扔进了马桶,连生产设备都报废了,可以算是鸡飞蛋打的典型。同例我们还可以参照美国歌星迈克尔.杰克逊,他现在一年要付给前妻300万美元,有一次差点就破了产。
说起婚姻的实质,连我这个独身主义者都替你们难过。人类的性供应时间不长,20岁开张,60岁打烊,也就40年左右的时间,听说有人七十多岁还能搞批发,我觉得那肯定是部长以上级干部,全靠补药顶着,要不然就是su-su-super猛男。40年是14000天,按三天一次计,人一辈子能消费的性资源不过4600单位。如果不生孩子,也不谈爱情,那么结婚其实就是为了这4600次。“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,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”,细细分析起来这事其实并不怎么浪漫,白首偕老,终生相伴,不过是4600次活塞运动的另一种说法。
为了使问题更好理解,我们对结婚的成本进行实证分析:
一、结婚的直接成本。北京人结婚时,前来道贺的小伙子会这么唱:“结婚了吧,傻冒了吧,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……”可见结婚要付出50%的收入,即使离婚也要按这个标准来分割共同财产。根据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说,消费取决于人一生的收入,我们假设一个人月收入1000元,工作40年的总收入是48万。48万一半自己用,一半拿来跟老婆换那4600次,平均每次也就是52块多。在这个问题上富人比穷人吃亏更大一些,如果月收入一万,那么性交的单价就是500多,据说莫斯科四星级酒店里就是这个价格,所以富人容易包二奶,因为每多包一个,他的成本就会降低一倍,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:决定夫妻关系并不是所谓的道德伦理,而是供需关系。如果你不巧是比尔.盖茨,那就太惊人了,按上述计算方式,你跟老婆亲热一次的价格是1100万美元,这钱如果买成猪肉,可以买16,000,000斤。
二、结婚的间接成本。胡塞尔说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不结婚的,这说明结婚要损失自由,裴多菲有诗道:为了自由,生命也可抛,爱情也可抛,可见自由是无价的,除了这无价的自由,你还必须在婚姻生活中花费大量的个人时间,比如陪老婆逛街,或者陪老公打麻将,这时间也是金钱;有人婚后感情不好,喜欢跟老婆吵架,说不定还要发生武斗,但不管是打坏了老婆,还是被老婆打坏,都要付出修理成本;如果被抓伤了脸,还要编谎话请假,产生误工成本;如果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,你可能要磨破几双皮鞋,经济学中把这种成本叫作“皮鞋成本”。
这么说来,婚姻就是一个大竹杠。批发本来应该比零售便宜,我们都知道商业采购的原理是“批量越大,成本越低”,现在可好,你一下子全包了,结果还被人狠狠敲了一竹杠。
当然,婚姻还有其他的价值,比如社科院的一个博士就说婚姻是人类繁衍的工具。我不大赞同这种说法,据我所知,人类繁衍靠的是性器官,而不是靠结婚证书。否则你去领个结婚证,再回家把那什么割了,看看能不能生出孩子来。要是生得出来,我情愿输你一本《葵花宝典》。照我看,婚姻不仅不能保证繁衍,反而大大有害于人类繁衍,我们都知道杂交水稻好,不仅长得壮,产量也高,五八年的时候据说一亩地能打几十万斤。而结婚即使有一千种好处,也掩盖不了这个致命的缺点:在婚姻的稻田里,你永远没法培育杂交品种。
(六)
在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之前,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怎样增加生产,避免出现饥荒。我们都知道,饥荒是生活基本资料、尤其是粮食的供应不足引起的,三年困难时期,因为高估产、高征收,再加上大办人民公社的过度浪费,弄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,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。
性爱市场也会产生供应不足的问题,对男性来说,女方不断提升的性技术、不断扩大的性需求真是个灾难。据说有个丈夫天天在汤里放安眠药,让老婆一吃完就呼呼大睡,不去想性供应和性需求的事,这法子可能有效,但实在是有点缺德:你万一把人家吃傻了怎么办?
供应不足如果严重了就会发生饥荒,有饥荒就会有逃荒者,这事就叫红杏出墙。平常人们对逃荒者总是很同情,除了安徽凤阳在1961打击过要饭的,说他们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大好形象,捉进去吊起来打,此外还真没见过这么没人性的。但对性爱逃荒者,人们却一直都很鄙视,说她们淫荡、道德沦丧、不守妇道,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潘金莲,人家不过就是在饥荒时吃了几口别人家的饭,就被道德学家们骂了一千多年,骂得人人自危,连慕容雪村这么大胆的人都有点哆嗦。这事其实是一个产权不清的问题,跟我们的国企改革差不多:潘金莲有没有权利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分配她的性资源?或者说,究竟谁是潘金莲性工厂的真正所有者?是她自己,还是武大郎?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,武大郎最多只有经营权,但你们非要连所有权都夺去,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猫匿,建议清河县反贪局介入调查。
我在企业里管过采购工作,一般情况下我都会选一家固定的供应商,定点采购的好处就是成本低、供应及时。但如果这家供应商供不上货,那我就要多找两家,这和潘金莲做的没什么区别,也没见谁说我淫荡或者道德沦丧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同情潘金莲,她和我一样都是优秀的采购员,关注采购质量,寻求足量、及时的供应,但我又加薪又升职,过得滋滋润润,潘采购却被公安局长武松一刀砍了,其间的迹遇,真是令人不胜嘘嘘。
前面说过了,经济学有时要研究如何增加生产,在这个问题上,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们有很多理论,比如提高劳动生产率,延长作业时间,还有费亨氏理论、德罗定律什么的,金正日将军提出还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,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科学技术,所以西门庆买了两个银托子,所以印度神油和龟鳖丸才会那么畅销,社会学家说性药泛滥是一个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,我觉得这事跟道德关系不大,我们卖春药只不过是为了避免饥荒,而众所周知,搞出饥荒可实在算不上什么道德高尚。
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。但说也奇怪,性工业应用科技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,反而是为了降低生产效率。说起“效率”这个词人人都明白,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做一件事,比的是谁更快,而在性爱问题上,人们却总想用最多的时间做那件事,比的是谁更慢。
(七)
经济活动会产生外部效应。关于“外部效应”,可以这么理解:比如办教育,除了能赚钱,还能提高国民素质,这“提高国民素质”就是一种外部效应,它是好的,所以叫作正的外部效应;开化工厂要污染大气,这是坏的,就是负外部效应。工厂污染大气,这是政府要管的事,所以要对化工厂额外收税,这种税最早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来的,就以他的名字命名,叫作庇古税。
我们的主旨是谈性。性产业的负外部效应十分明显,前段时间澳大利亚有家妓院上市,我到他们的网页上浏览了一下,发现满页都是黄色图片。我这个人虽然趣味低下,自制能力还是有的,所以看了也不会? |
|
|
|
|
 |
|
|










 不羁风云
不羁风云 



 转自行业热点的一篇文章[2006-6-4 15:26:00]
转自行业热点的一篇文章[2006-6-4 15:26:00]